-
硅在土壤中含量丰富,在增强植株机械性、抗逆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2]。土壤中能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有效硅含量常被作为衡量土壤硅植物有效性的指标。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南方森林土壤酸化不断加剧,亚热带森林土壤中的有效硅随环境因子的不断改变呈明显的下降趋势[3],这也使森林土壤有效硅对环境因子的响应成为当今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其研究对于通过调控环境因子以改变土壤硅形态,从而提高植物利用有效硅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土壤有效硅主要来源于土壤中无机硅(包括晶态硅和可提取态硅)的分解和解吸[4-5],其中,晶态硅多为难以在土壤中分解的硅酸盐矿物及二氧化硅,可提取态硅则主要包含水溶性硅、活性硅及无定形硅[6]。与状态较稳定的晶态硅不同,各可提取态硅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水溶性硅及活性硅更是大量包含了能被植物直接吸收的单硅酸及易于转变为单硅酸的组分,这也使土壤可提取态硅含量及其转化关系与土壤硅素植物有效性密切相关[7],环境变化可能通过影响土壤可提取态硅间接作用于有效硅。
研究表明,温度、降水量等气候因子对土壤中各形态硅的含量存在一定影响[8],而海拔变化能够使多种与植物生长发育存在紧密联系的气候因子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呈现梯度性改变,研究土壤硅形态与海拔变化的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土壤硅对环境变化的响应。除气候因子外,土壤硅素同时受到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如土壤有效硅含量与土壤pH值往往呈正相关关系[9-10]。因此,在以海拔变化为主导的小尺度空间内,通过对海拔及其他土壤理化性质与土壤硅形态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可较好地揭示土壤硅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随着我国南方地区森林有效硅含量的下降及森林生态系统中硅素重要性的日益凸显[11],对南方森林土壤硅素进行研究有着愈发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对于土壤硅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水稻(Oryza sativa L.)、毛竹(Phyllostachys edulis (Carriere) J. Houzeau)等硅富集植物生长的土壤[12-13],关于亚热带地区常见的常绿阔叶林土壤中各硅形态变化特征的研究鲜见报道。栲树(Castanopsis fargesii Franch.)作为壳斗科(Fagaceae)锥属(Castanopsis (D. Don) Spach)乔木,主要分布于亚热带海拔200~2 100 m坡地或山脊杂木林中[14],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主要建群树种之一。郭岩山自然保护区位于福建省顺昌县,各海拔均生长着以栲树为建群种的常绿阔叶林,且地势险峻,各环境因子随着海拔升高往往呈现出梯度性变化[15],这也使其成为研究环境变化对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土壤硅素影响的适宜地点。本研究拟通过对郭岩山不同海拔环境变化下的栲树林分土壤硅形态的含量及硅形态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揭示土壤硅形态在亚热带山地的空间变化规律及土壤硅形态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明确不同土壤硅形态在植物生长中发挥的作用,为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栲树林乃至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有效利用土壤硅素提供理论参考。
-
郭岩山自然保护区是福建省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属于南平市与三明市的交接地带(27°06'~27°18'N,118°00'~118°30'E),主峰高达1 383.7 m,是顺昌县第一高峰。郭岩山自然保护区地处亚热带地区,属海洋性季风气候[16],四季分明,无酷暑与严寒,年降水量和日照充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水热条件使郭岩山自然保护区植物资源丰富。区内主要树种有栲树、青冈(Cyclobalanopsis glauca (Thunb) Oerst)、毛竹、木荷(Schima superba Gardn et Champ)等,而栲树则为郭岩山地区分布最广,也是最重要的建群树种。
-
郭岩山自然保护区天然栲树林分布集中于海拔600~1 000 m,本研究从600 m开始随机布置样地,每间隔100 m设置1个海拔,每个海拔设立5个30 m × 30 m的试验样地。为了消除林分边缘林木的影响,调查过程中以距离样地边缘5 m的地段作为缓冲区,采用相邻网格法进行样方布设,将样地平均分为36个5 m × 5 m的样方,对网格小样方进行行列号(x,y)的编号后,对每个小样方中胸径大于或者等于5 cm的植株进行每木调查,测量胸径、树高等因子,对于胸径(地径)小于5 cm的乔、灌木或草本植物,只记录其坐标、种类及数量(盖度)等信息。海拔由手持多功能电子高度计测得,样地基本概况详见表1。
海拔
Altitude/m林分特征
Stand characteristics土壤特征
Soil properties平均胸径
Average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cm平均树高
Average tree
height/m林分密度
Stand density/
(株·hm−2)全碳
Total C/
(mg·g−1)全氮
Total N/
(mg·g−1)全磷
Total P/
(mg·g−1)600 13.3 ± 1.12 12.0 ± 1.98 450 ± 32 23.33 ± 9.51 1.89 ± 0.61 0.44 ± 0.14 700 15.1 ± 0.98 13.5 ± 1.55 338 ± 16 20.21 ± 10.62 1.73 ± 0.70 0.26 ± 0.08 800 13.9 ± 2.28 11.0 ± 1.12 381 ± 21 28.52 ± 12.21 2.43 ± 1.19 0.43 ± 0.14 900 12.5 ± 0.91 10.5 ± 1.22 300 ± 15 35.76 ± 10.58 4.31 ± 1.31 0.33 ± 0.19 注:表中平均胸径、树高和密度均为栲树数据。
Notes: Mean DBH, tree height and density in the table are data of Castanopsis castanopsis Fransh.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plots
-
在每个样方中随机选取5株生长状况良好、树形基本一致的栲树,以栲树干基部为中心,沿地表径流的方向,去除腐殖层后在上坡位和下坡位各分层采集0~20、20~40、40~60 cm土层内的土壤样本,将上坡位和下坡位样本混合以消除坡位差异,围绕样方内挑选的5株栲树重复采集5次,采集后部分土壤放至超低温(−80 ℃)冰箱冷藏,部分风干15 d后用于测定土壤理化性质。同时,在各土层采集环刀样品,当天称质量并密封,用于测定土壤容重。
-
本研究仅针对易于被植物吸收的土壤可提取态硅进行研究,而土壤晶态硅多为难以在土壤中分解的硅酸盐矿物及二氧化硅,无法被植物直接利用,与本研究内容相关性较小,故对包括晶态硅的土壤总硅含量不进行测定及分析。
-
pH值4.0 HOAc-NaOAc缓冲液浸提,土液比1:10,40 ℃振荡5 h,振荡完成后的液体利用针管通过0.45 μm过滤膜,于塑料瓶中保存待测。
-
0.02 mol·L−1 CaCl2浸提,土液比为1:5,25 ℃振荡12 h,振荡完成后的液体利用针管通过0.45 μm过滤膜,于塑料瓶中保存待测。
-
pH值1.5的0.5 mol·L−1 CaCl2浸提,土液比1:10,25 ℃振荡12 h,振荡完成后的液体利用针管通过0.45 μm过滤膜,于塑料瓶中保存待测。
-
0.5 mol·L−1NaOH煮沸5 min,土液比1:10,煮沸后冷却的液体利用针管通过0.45 μm过滤膜,于塑料瓶中保存待测。
-
利用FeSO4还原-硅钼蓝比色法测定土壤硅形态含量。取塑料瓶中滤液5 mL于5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15 mL左右,依次加0.6 mol·L−1 1/2 H2SO4 5 mL, 50 g·L−1钼酸铵5 mL,摇匀后放置10 min;再依次加入50 g·L−1草酸液5 mL,50 g·L−1硫酸亚铁铵5 mL,用水定容。放置20 min后,在分光光度计上(波长700 nm)1 cm光径比色皿比色。
式中:c为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硅(Si)浓度(mg·L−1),V为显色液体积(50 mL),D为分取倍数,(D = 加入浸提剂的体积/吸取浸提液体积),m为试样质量(g)。
-
参考我国森林土壤测定国标法和土壤分析技术指南[17]测定土壤pH值、孔隙度、有机质和容重、碳、氮、磷的全量;土壤全碳、全氮用碳氮元素分析仪(Vario Max Elemental Analyzer,Germany)测定;磷全量养分通过混合酸消煮后用连续流动分析仪(San + + ,Skalar,Netherlands)测定;pH值用电位法测定;土壤孔隙度用容重换算法测定;有机质用水合热重铬酸钾氧化-比色法测定;容重用环刀法测定。
-
试验数据收集整理后,用SPSS的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检验不同海拔不同土层硅形态差异的显著性,用SPSS对各形态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用通径分析方法分析不同形态硅对有效硅的贡献程度,用Canoco5对土壤理化性质与土壤硅形态进行冗余分析及回归分析。图表中数据采用5个重复的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采用Origin 2021软件进行作图。
-
郭岩山自然保护区不同海拔土壤硅形态含量存在较大差异,含量由高至低依次为无定形硅(1 448.12 mg·kg−1) > 活性硅(273.39 mg·kg−1) > 有效硅(120.79 mg·kg−1) > 水溶性硅(117.90 mg·kg−1)。各硅形态在海拔及土层梯度上的变化特征(图1)表明:从不同海拔看,高海拔处(900 m)土壤有效硅、水溶性硅、活性硅及无定形硅含量均显著高于低海拔(600 m);中海拔(700~800 m)土壤有效硅及土壤无定形硅含量显著高于低海拔(600 m);土壤水溶性硅及活性硅含量在中低海拔内的变化相对较小,仅800 m的0~20 cm土层内活性硅及水溶性硅含量显著高于600 m和700 m处。
各海拔中硅形态在不同土层间的分布特征不同:除800 m海拔处,土壤有效硅含量在各海拔各土层均差异显著,大小依次为40~60 cm > 20~40 cm > 0~20 cm;土壤水溶性硅含量在各土层间差距较小,仅900 m海拔处0~20 cm土层水溶性硅含量显著高于40~60 cm土层;土壤活性硅含量在600 m和700 m海拔处深土层(40~60 cm)均显著高于0~20 cm和20~40 cm土层,而800 m和900 m处各土层土壤活性硅含量差异不显著,与600 m和700 m海拔处特征不同;除600 m海拔外,土壤无定形硅含量在各海拔不同土层间均差异显著,呈0~20 cm > 20~40 cm > 40~60 cm,且各海拔处的浅土层(0~20 cm)无定形硅含量均显著高于深土层(40~60 cm)。
-
由表2可知:土壤水溶性硅含量与有效硅、活性硅及无定形硅含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P < 0.01),土壤有效硅含量与活性硅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P < 0.01),与无定形硅含量无明显相关,土壤活性硅含量与无定形硅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性(P < 0.01)。
项目
Item水溶性硅
Water soluble silicon有效硅
Effective silicon活性硅
Active silicon无定形硅
Amorphous silicon水溶性硅 Water soluble silicon 1 0.512** 0.756** 0.527** 有效硅 Effective silicon 0.512** 1 0.695** 0.209 活性硅
Active silicon0.756** 0.695** 1 0.408** 无定形硅 Amorphous silicon 0.527** 0.209 0.408** 1 注:**表示相关性极显著(P < 0.01)
Note: **Indicates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 < 0.01)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silicon forms in soil
-
相关性分析表明:土壤硅形态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但简单的相关分析不能比较各形态硅对有效硅的贡献程度,而通径分析能将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互影响分解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为进一步分析可提取态硅对有效硅的贡献程度及方式,对可提取态硅与有效硅间进行通径分析,表3表明:各可提取态硅对有效硅的直接通径系数(D)的绝对值从大到小依次为:活性硅(D2Y = 0.721)、无定形硅(D3Y = −0.094)和水溶性硅(D1Y = 0.016)。在间接通径系数的绝对值中,以活性硅通过水溶性硅对有效硅的间接通径系数(0.545)最大,活性硅通过无定形硅对有效硅的间接通径系数(0.294)次之。这表明活性硅是有效硅增加最重要的直接贡献形态,而水溶性硅是土壤硅转化过程中的重要过渡性硅形态。
因子
Factor相关系数
Pearson直接通径系数
Direct path
coefficient间接通径系数 Indirect path coefficient X1→Y X2→Y X3→Y 合计 X1 0.512 0.016 0.0121 0.008 0.021 X2 0.695 0.721 0.545 0.294 0.839 X3 0.209 −0.094 −0.049 −0.038 −0.088 注:决定系数(R2) = 0.490。X1、X2、X3、Y分别代表水溶性硅、活性硅、无定形硅及有效硅。
Not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 = 0.490. X1, X2, X3 and Y represent water-soluble silicon, reactive silicon, amorphous silicon and effective silicon, respectivelyTable 3. Path analysis of different forms of silicon and available silicon content in soil of natural Castanopsis fargesii forest in Guoyan Mountain
-
对土壤各理化性质和土壤硅形态进行冗余分析,由图2可见:第1轴和第2轴的特征值分别为0.195 8、0.094 6,土壤理化性质解释了30.5%的土壤硅形态含量变化。第1、2排序轴包含95.89%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硅形态的信息,其中,第1排序轴和第2排序轴分别占总信息量的64.98%、30.91%。图2显示:无定形硅与土壤容重、pH值呈负相关,与土壤孔隙度、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及全碳呈正相关;水溶性硅与土壤孔隙度、土壤有机质、全氮及全碳呈正相关,与容重呈负相关;活性硅与土壤孔隙度、pH值、全碳及全氮存在正相关,与土壤有机质和容重呈负相关;土壤有效硅与pH值、容重及全氮呈正相关,与土壤有机质、全磷、全碳及土壤孔隙度呈负相关。
由表4看出: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硅形态的含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土壤有机质和pH产生的影响极显著,解释率分别达14.1%和9.2%,贡献率分别达46.2%及30.2%,与硅的含量具极显著相关性(P < 0.01),其次为容重、全磷、全氮、全碳及土壤孔隙度,各自解释了2.4%、1.8%、1.6%、0.9%和0.5%的土壤各硅形态含量的变化。
土壤理化性质
Soil physi-chemical properties解释率
Explanatory rate/%贡献率
Contributing rate/%F P 有机质 Organic matter 14.1 46.2 13.3 < 0.01 pH 9.2 30.2 7.4 < 0.01 容重 Bulk density 2.4 7.8 2.3 0.10 全磷 Total P 1.8 6.0 1.8 0.19 全氮 Total N 1.6 5.1 1.5 0.17 全碳 Total C 0.9 3.0 0.9 0.34 孔隙度 Porosity 0.5 1.6 0.5 0.63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il physi-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oil silicon forms
-
郭岩山土壤硅含量在海拔、土层梯度上均呈现垂直分布特征:高海拔(900 m)土壤各硅形态含量均显著高于低海拔(600 m)。究其原因是随海拔升高,大气温度逐步下降,导致土壤中水分不易被植物吸收[18]或蒸发,造成植物生长速率降低,吸收土壤硅的速度减缓,从而降低了植物对土壤有效硅的利用率,这与Hidehiro等[19]对土壤硅有效性的研究结果一致。高海拔(900 m)处水溶性硅及活性硅含量显著高于低海拔(600 m),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水溶性硅及活性硅不仅受高海拔处因温度下降使硅酸溶解缓慢的影响,且与受温度影响植物吸收硅效率下降有关[20]。
各海拔中不同土层间硅含量差异明显[21]:深土层(40~60 cm)土壤有效硅含量显著高于浅层土(0~20 cm),可能是由于表层土壤(0~20 cm)容重较小,土壤孔隙较大,土壤有效硅易于向土壤深层堆积;土壤水溶性硅在中低海拔(600~800 m)各土层间均无显著差异,原因是水溶性硅可溶于土壤溶液中,在土层间具有流动性且常以单硅酸形式存在;而浅土层(0~20 cm)无定形硅含量均显著高于深土层(40~60 cm),是由于植物凋落死亡分解部分大多数会以无定形硅返还回土壤中[22],这与Klotzbücher等[23]对土壤有效硅含量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土壤表层中的无定形硅含量相对较高,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有机物输入减少,无定形硅含量随之下降[24]。
-
可提取态硅对植物具有重要意义,其硅形态主要包含水溶性硅、活性硅及无定形硅,其中,活性硅常以交换态硅及胶体态硅存在于土壤中,与水溶性硅保持着动态平衡[7]。本研究表明,郭岩山土壤水溶性硅含量与活性硅、无定形硅及有效硅含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土壤活性硅含量与无定形硅及有效硅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性。其原因是可提取态硅中主要以无定形硅为主[25],能够水化形成胶体态硅或溶解于土壤溶液中,提供部分利于植物生长所吸收的有效硅。可提取态硅的各个组成部分可通过不同的方式相互转化,从而达到动态平衡[26]。土壤硅各形态间存在相关关系,这与蔡彦彬等[27]对不同土壤硅形态含量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进一步的通径分析结果表明,活性硅对土壤有效硅的直接通径系数绝对值最大,表明活性硅是有效硅增加最重要的直接贡献形态,其原因是活性硅含有交换态及胶体态硅,其中一部分是易于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单硅酸或可转化为单硅酸的成分[28];而有效硅与水溶性硅的间接通径系数相对较大,表明水溶性硅是土壤硅转化过程中的重要过渡性硅形态,原因是水溶性硅能解吸成交换态硅或聚合成胶体态硅,而后转化为活性硅间接提供植物生长所需的有效硅[7]。由此可见,相比于其他硅形态,活性硅对调控亚热带森林土壤的硅循环具有重要作用[6],可能成为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亚热带森林土壤中有效硅的重要来源。
-
硅作为土壤中第二丰富的元素,其在土壤中含量的高低会改变植物对硅养分吸收的策略。此外,土壤供硅能力亦受到土壤质地、温度、土壤元素等理化性质的影响[29]。本研究表明,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硅形态含量及有效性存在一定影响:土壤有机质与无定形硅及水溶性硅呈正相关,与土壤活性硅及有效硅呈负相关,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土壤有机质会覆盖吸附态硅[30],使其难以释放到土壤中,也可能是因为黏粒的专性吸附点由于复合物的包被作用而减少,导致硅酸盐无法被吸附而损失,造成土壤有效硅及活性硅含量减少,无定形硅及水溶性硅含量增加;土壤pH值与土壤各硅形态含量存在不同程度相关性,pH值与土壤活性硅及有效硅含量呈正相关,随着土壤pH值的增加导致淋溶作用减弱,土壤中的硅便不易被淋失[31];而无定形硅含量与pH值呈显著负相关,这是由于长期的风化作用导致无定形硅含量损失,这与李巧玲等[32]、向万胜等[33]对土壤硅形态与pH值关系的研究结果一致。土壤容重与土壤水溶性硅、无定形硅含量呈显著负相关,而土壤孔隙度与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可能是因为疏松多孔的土壤往往有较高的含水率,因而可以溶解更多的水溶性硅,而可提取态硅各形态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动态平衡,进而影响无定形硅含量[34]。受限于试验区域条件限制,研究仅反映了亚热带栲树林天然林林分土壤硅形态特征,而在其他不同建群种的亚热带天然林林分中,土壤硅形态是否也存在相似特征?仍有待于进一步扩大研究区域范围以验证。
-
(1)在海拔梯度上,高海拔(900 m)的土壤各可提取态硅含量均显著高于低海拔(600 m);(2)土壤水溶性硅含量与有效硅、活性硅及无定形硅含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土壤活性硅含量与有效硅及无定形硅含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其中,活性硅是有效硅增加最重要的直接贡献形态,水溶性硅是土壤硅转化过程中的重要过渡性硅形态;(3)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各硅形态存在影响,其中,土壤有机质含量和pH值产生的影响最显著,其对土壤硅素变异贡献率分别达46.2%和30.2%。
Soil Silicon Form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Castanopsis fargesii Forest at Different Altitudes in Guoyan Mountain
- Received Date: 2022-09-20
- Accepted Date: 2022-11-07
- Available Online: 2023-04-20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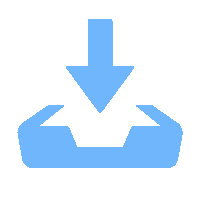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
